放大资金,增加盈利可能
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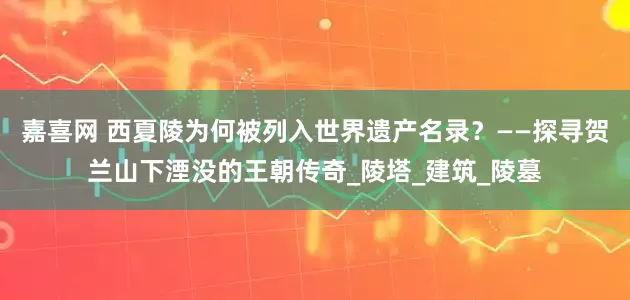
□李伟元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中国申报的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增加到60项。西夏陵不是一座单独的陵墓,而是由9座西夏帝陵、271座陪葬墓、32处防洪遗迹、5.03公顷建筑基址、7000余件出土文物共同组成的考古遗址,遗产保护区近40平方公里。
自1038年至1227年,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曾在我国西北地区雄极一时。“西夏”是宋人对它的称呼,西夏人自称“大白高国”。这一政权虽然未能列入二十四史,仍然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9座西夏帝陵主人的身份是否已经揭晓?陵墓和出土文物又展示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贺兰山下古冢稠 云是昔时王与侯
在贺兰山东麓的山前洪积扇地带,9座帝陵有序排列,东望滚滚黄河,西北依莽莽山峦。尽管在西夏灭亡时遭到严重破坏,又经历了八百余年沧桑,仍然可见其恢宏的气势。
展开剩余86%西夏立国190年以来,共经历了10任帝王统治,加上被追封为太祖、太宗的李继迁和李德明,帝陵应葬有12位帝王。为何仅有9座帝陵?由于王朝末年风雨飘摇、战乱频仍,西夏的最后三位皇帝来不及建造帝陵,便遭遇灭国之灾。实际上,西夏陵的帝陵数量和《宋史·夏国传》的记载是吻合的,即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德明嘉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谅祚安陵、惠宗李秉常献陵、崇宗李乾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陵、桓宗李纯佑庄陵、襄宗李安全康陵,但《宋史》并未记载各帝陵的具体位置。据说在明代时,当地人已经不知西夏陵所葬者为何人,在口耳相传中,残存的帝陵都是景宗李元昊的“疑冢”。
自20世纪70年代起,学界对西夏陵开展调查和考古发掘,根据中国古代传统葬仪的左昭右穆制度,对帝陵按排列顺序予以编号,其中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和九号陵位于平原上,四号、六号和八号陵依山而建。目前,仅有七号陵的墓主身份得以确认,根据出土残碑的西夏文碑额“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确定其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印证了这一排列法。由此推断,占地规模最为宏大、建筑最精美的三号陵墓主应为西夏开国皇帝景宗李元昊。
从西夏陵的选址,亦可一窥传统风水堪舆之学对西夏的深厚影响。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在风水学中被称为“前有饮马塘,后有跑马岗”,地面主要为排水良好的砾石、粗砂,地质结构紧密,经历多场地震,陵墓仍然安然无恙。西夏陵中的32处防洪遗迹,更是重要的古代防灾实物资料。尽管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每年夏季仍然有集中降雨的情况,西夏陵所在位置更是容易遭遇一过性的洪水冲刷,因此在建陵伊始,便设计了专门的防洪措施。在地势较高的区域,砌有阻挡山洪的防洪墙,地面则根据地形走势,向下开挖疏导雨水的排洪沟,共同保卫着西夏陵的安全。
西夏陵中的每座帝陵均由三面或四面围合而成的陵城和月城相连组成,平面布局类似倒“凸”字,外围建有夯土城墙,内部建有角台、阙台、碑亭、献殿、陵塔等地上建筑,陵城地下建有墓道、墓室,各陵园结构大体相同。明代胡汝砺著《弘治宁夏新志》载:“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嘉裕诸陵是也。其制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已无一物矣。”“数冢巍然”,所指的正是西夏陵中最为醒目的夯土建筑“陵塔”,用黄土混合砾石,层层夯筑而成,其中最高的有20余米。由于它们的外形略像古埃及的法老陵墓“金字塔”,也有人将西夏陵塔比喻为“东方金字塔”。或许有人会望文生义,想当然地认为,这9座夯土陵塔就是高大的坟墓,墓室肯定藏在土堆的下面。实际上,这些土堆是守卫墓葬的陵塔的残余部位,与墓葬还有10米左右的距离。陵塔均为实心结构,位于陵城西北隅、墓室正后方,是西夏特有的葬俗。在陵塔刚被建造出来的时候,七层八角,红墙密檐,脊兽镇顶,风铃叮咚,既有皇家的庄严,更展现出西夏对佛教的尊崇。如今,陵塔的外部装饰早已不复存在,仅有内部的夯土坚固如昔,致密的质地令野草都无法在上面扎根。
西夏陵的271座陪葬墓没有帝陵专有的角台、阙台等建筑,规模、形状、使用的建筑材料也与帝陵有着明显差距。墓主虽大多身份不明,但可以确认的是,他们或为皇亲国戚,或为达官显贵。目前仅有一座陪葬墓发现了残存的碑文,能够证实此墓主人为西夏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嵬名”为皇族姓氏,此人在崇宗李乾顺统治时期任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等要职,并主持整修过西夏都城中兴府。
塞外龙吟久已杳 清歌犹忆妙音鸟
虽然在历史上经历过大规模盗掘,西夏陵仍然出土了种类多样的文物,包含石雕、金属制品、纺织品、陶瓷、琉璃或陶制的建筑构饰件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体现出西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深度吸纳融合,也证实了西夏对东西方丝绸之路贸易的维系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是帝陵遗址出土的鸱吻。作为我国古建筑屋脊上的重要构件,鸱吻通常位于大殿正脊的两端,形如龙头,张口吞脊,也写作“螭吻”。鸱吻古称鸱尾,汉武帝时即有记载,称“海中有鱼虯,尾似鸱,激浪即降雨”。古人认为以海中鱼形为饰,可以避火,后来宫廷鸱吻演变为龙首鱼身造型。鸱吻不仅是吉祥的装饰,还能起到固定和支撑作用,通常安装在正脊两端与向屋檐四角延伸的垂脊的相交之处。西夏帝陵出土的鸱吻中,最大、最完整的一座为绿釉琉璃材质,高152厘米,躯体遍布鱼鳞纹,龙头约占鸱吻总高的一半,瞪眼张口,气势威武,有着独特的粗犷风格。
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构件中,还有一种陶塑构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它的上半身为人形,头戴花冠,双手合十,身披璎珞,背上双翼舒展,下半身为鸟形,长尾高翘,双爪蜷伏。这一形象就是佛教中的“迦陵频伽”,意为“妙音鸟”,以鸣声美妙著称。尽管迦陵频伽造型的绘画、雕塑在中原并不少见,但通常只在寺庙佛殿中做装饰,西夏却将它安装在陵园建筑的屋顶垂脊或戗脊最前端,体现出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尊崇。
被誉为宁夏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鎏金铜牛,出土于陪葬墓中,长1.2米、重188千克。铜牛中空,造型屈腿卧地,栩栩如生,体现出高超的冶炼、浇铸、鎏金等金属加工工艺。出土时,在它对面还有一件大小相仿的石马,同样为卧姿。铜牛头朝墓室方向,石马头朝墓道入口,可能分别代表着维系国家根基的农耕和征战,令人怀想起西夏强盛时的景象。
千古兴亡多少事 党项豪雄今何处
西夏王朝的建立者属于党项族,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东汉《说文解字》记载:“羌,西戎牧羊人也。”党项人又称“党项羌”,以畜牧为业。党项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在青海东南部的“黄河九曲”,隋末唐初扩展到今青海、甘肃、四川松潘高原一带,唐时受吐蕃所迫,北上迁居到今宁夏、陕北、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等地。
党项部落首领本姓拓跋氏,唐朝初年,西夏皇族的祖先、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协助吐谷浑与唐军作战,不敌而降,被唐太宗封为西戎州都督。唐末黄巢起义时,党项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率军协助讨伐,因收复长安有功,诏封夏国公,赐姓李,后又“赐夏州号定难军”,统领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范围大致包括现在陕北和与之接壤的内蒙古部分地区,“虽未称国,而自王其土”,为后来西夏立国打下了基础。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李思忠)相传勇力过人,在与黄巢作战时战死,追赠宥州刺史,他就是西夏太祖李继迁的高祖父。
自五代至北宋初年,党项人始终依附中原,首领先后被五代各朝、宋朝封为节度使。宋太宗统治时期,夏州政权归宋,首领李继捧被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向宋朝献出五州之地。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带领党项族各部叛宋,自立政权,与辽结盟,被辽朝册封为夏国王。宋廷为招抚李继迁,曾对他和李继捧赐姓赵,李继迁被赐名“赵保吉”,这也是夏景宗李元昊在北宋史籍里有时被写作“赵元昊”的缘故。但这一怀柔政策并没有阻挡李继迁叛宋的进程,他先后收复五州,在1002年攻下军事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改名西平府,在此建造宫室、宗庙。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被辽封为西平王,采取“依辽和宋”政策,麻痹辽、宋,暗中不断扩张国力、巩固政权,并将政治中心由西平府迁至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后来成为西夏国都兴庆府。
李德明长子李元昊在1032年即位后,展现了勃勃野心。他不甘臣服于宋,在1038年自立为帝,建国号为“夏”,宋朝称为西夏。李元昊废除唐、宋所赐的李姓、赵姓,为皇室改姓“嵬名”,自己改名“曩霄”,对外自称“兀卒”,意为“青天子”。《宋史》记载:“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续资治通鉴》将“兀卒”写为“乌珠”:“但欲自称乌珠之号,当国者虑害不深,吝此虚名,遂成实祸。”
李元昊作为开国之主,文治武功颇有建树。他开疆拓土,大体形成了西夏“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疆域轮廓,在他统治时期,西夏与宋作战三年,在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穆桂英挂帅”里,穆桂英五十三岁再领帅印,出征的对象便是西夏。宋夏战争中,宋军遭遇三次大败,史称“镇戎三败”,西夏也元气大伤,民怨沸腾,双方最终在1044年签订“庆历和议”。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两、丝绢、茶叶,西夏向宋称臣,李元昊接受宋的封号,实际上对内依旧以皇帝自称。李元昊还全面学习宋朝制度,为西夏订定官制、军制、法律,命大臣野利仁荣模仿汉字结构和基本笔画创制西夏文,定为“国字”,史称“蕃书”。今天,宁夏贺兰县尚有“李王渠”遗址,是李元昊在位时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渠长300余里,引黄河水灌溉宁夏平原,“岁无旱涝之虞”。
李元昊虽有雄才大略的一面,更有暴戾独断的一面。因其母族首领卫慕山喜谋反,他将卫慕全族沉于黄河,据说还毒死了自己的母亲卫慕氏。李元昊最终自食其果,晚年夺占太子妃没移氏,废皇后野利氏为庶人,太子宁令哥为报仇,将李元昊刺伤致死。国相没藏讹庞以弑君罪名处死宁令哥和其母废后野利氏,拥立李元昊的幼子李谅祚即位,没藏讹庞的妹妹没藏氏成为摄政太后,开启了一段女主专政的时期。历数西夏毅宗、惠宗、崇宗三朝,三任太后连续独揽大权,体现了西夏妇女在政治上较为突出的地位。
经历数代传承,西夏先后周旋于宋、辽、金、元之间,既有交战,亦有修好,最终被为元所灭。因西夏抵抗强烈,元太祖成吉思汗四次亲征,最终死于征讨西夏途中,在民间传言中,他为西夏军的毒箭所杀。诸将遵照元太祖遗命,将西夏末代皇族尽数诛杀。更名为中兴府的国都被元军大肆劫掠,皇宫、陵寝、典籍、史料毁坏殆尽,元朝后来也未为西夏修纂国史,仅在宋、辽、金三史中各有“夏国(西夏)传”或“西夏外纪”。
不过,西夏虽然灭国,遗民并没有彻底消亡。党项人成为元朝的子民后,被归为“色目人”,一部分仍然居于故地,还有部分党项人迁移到其他地区。1962年,在河北保定市韩庄乡发现了明代弘治年间刻有西夏文的陀罗尼幢石碑,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晚的西夏文实物,体现出在明代的北直隶仍然有一定规模的党项人聚居。另外,分布在四川贡嘎山区的木雅藏族保留着和西夏相似的服饰、建筑,语言也和传统藏语有区别,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南迁的党项人后裔。可以确定的是,党项人已经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再作为单一的民族存在了。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发布于:山东省美港通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